曹植诗赋中表达的爱情非常丰富,共计22篇。其中诗歌16篇,赋6篇。有初次携手的喜悦、有一同游玩的欢乐、有两地隔绝的相思、有相互的猜忌与解释、有无法求婚的忧伤、有生死相思的真挚与苦痛,有失去爱的女子的悲哀。是建安文人诗中,第一个大力开拓爱情世界的人。曹植的诗赋中写到了男女相聚时的快乐。在《芙蓉赋》中有初次牵手的感动,《芙蓉赋》开篇写芙蓉的美丽,而“观者终朝,情犹未足”,写出了共同观赏芙蓉之后,二人仍不满足,便有了采芙蓉的行为,“狡童媛女,相与同游。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其中更是欣喜地写下了那初次牵手的悸动,“擢素手于罗袖,接红葩于中流”便成了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在曹植的爱情诗赋中,有些诗赋充满着因阻隔而无法结合的绝望。在曹植的爱情诗赋中,总有很多阻隔的爱情,其中包括空间的阻隔,例如:杂诗其一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一句之中,“万里”是相隔之远,“迥且深”的江湖是无法逾越,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是鸿雁,然而那哀鸣的鸿雁也“形影忽不见”,无法为自己传递音讯,在这里离思被阻隔的绝望放大了。

曹植爱情的阻隔还在于由于缺少沟通之人——良媒,无法由相思转化为合理的接触与婚姻。在曹植的爱情诗赋中,“无良媒”造成了曹植爱的接触的不合理,使其爱恋成为单相思,更是阻断了婚姻的可能。曹植的诗歌,亦有从女性的视角写对男子的思念与爱恋。比如《闺情》其一:写曾经喜乐与共,“春思安可忘,忧戚与君并”,如今自己孤单独守空闺,“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由于以往的欢会很难再次实现。不由得让人担忧:“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自己就像寄托在松树上面的女萝,像依水的浮萍一样飘摇不定。然而自己仍然“赍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以不变的赤诚等待男子的归来。“傥终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如果能换来、等来男子的回顾,这是最符合我内心的爱恋的。曹植对女子内心的体味可谓细致入微,将女子对意中人的思念写得百转千回、缠绵悱恻。而在《朔风诗》中更是写了分离双方的思念。

在曹植的诗作中有一些从女方着笔,体贴对方忧愁的诗作,这本得益于建安年间,曹丕倡导的代女性言情的诗歌拟作潮流。曹植此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是《七哀诗》诗中女子虽然未被休弃,然而“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处于被抛弃的状态,痴情的女子明白“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一为清尘一样飘摇而上,一为浊泥一样不断下沉。怎么能和谐呢?可是自己仍然想像风一样投入到您的怀中,你却不接纳我,让我依赖谁呢。此诗视角由外而内,先写女子月夜无眠,独自悲叹,继而以问答的形式引出女子独白,表达了女子被抛弃后感到孤寂,以及男女之间距离日渐扩大无法会合,表达了女子的一腔柔情被拒的悲哀。

在曹植的赋中,亦有弃妇诗。此类作品多为代言,曹丕等人均有创作,是曹植应曹丕之邀而作。《出妇赋》写“无愆而见弃”的女子,赋作从初婚写起,直至男子“悦新婚而忘妾”,然后重点写自己的伤痛,“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衣入门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仆御而登车,左右悲而失声。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代刘勋妻王氏见出为诗》:“人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写出了弃妇对休弃自己的人并没有怨恨,相反仍心存亲情。而《弃妇篇》则代被休弃的刘勋妻抒情,《玉台新咏》注:“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借石榴无子写了因无子被休的女子的忧伤,其中有对“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不公的控诉,有彻夜无眠、踟蹰屋舍、抚弦调筝,想要摆脱却无法排遣的忧愁。这类诗赋虽然是代言体,却能细致入微地体会失意女性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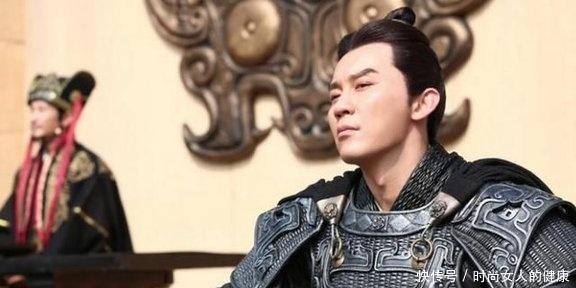
在曹植爱情主题赋作中,成就最高的为《洛神赋》,在《文选》“情类”中,共计列入了四篇赋作,分别是:《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其中《洛神赋》晚出,被认为是“情类”的代表,亦即当时爱情赋的代表。今人袁行霈先生甚至认为(爱情赋)“以《洛神赋》为顶点”。《洛神赋》之自我深情与前三赋所叙之探讨男女人性吸引泛泛之情有着泾渭之别,《洛神赋》中的爱情书写因而呈现出突破性的特征,因而,《洛神赋》中呈现的爱情世界以及爱情书写的特征具有特殊的意义。

《洛神赋》的基础是守礼,守礼中不时有违礼的情感透出,“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中直接点明其习礼明诗,且应允的前提是“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直指死后好合。“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感情不可遏止地喷涌而出,连用“恨”、“怨”二字领起,“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在人神道殊不得相爱的情况下、情感是难以抑制的,“盛年莫当”点出了最好的年华却不能在一起的遗憾深深。最终“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更是情突破礼,生死相恋的呐喊。

汉代是一个士人的个体情感受到外在世界与内心自觉双重压制的时代,“一般士人是不能作诗的,更不敢想象以诗歌写作个人的喜怒哀乐,写作一己的日常生活,更是万万不能想象以诗歌写作自我真实的情爱,特别是不伦的恋情思念。”曹植承此背景之余风,其《洛神赋》借用传统情类赋《高唐赋》《神女赋》的男女遇合模式,表面上仿佛仍然探讨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似的人性之欲与道德自守,实则是将曹植甄后的现实爱情经历、情感体验放置于黄初三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书写,从而使情类赋由书写空泛的情感与哲思,转向了作者自身经历的个体化言说,曹植于其中表现了与甄后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在《洛神赋》中所表现的男子求爱得到允可之后的担忧,被拒绝之后的接触与恋慕、以及在女主人公死后的倾情怀念极具个性化特征;女主人公的大胆接受求爱、对犹豫退缩的男子的同情与体贴、以及对男主人公交往要合礼的告诫、至死不渝的爱情也打下了甄后鲜明的烙印。也正是因为对现实人生的书写,才突破了传统赋作的概念化的表达,而书写了一个更加复杂曲折的爱情经历,抒发了在爱情追求与礼的夹缝中人的心灵的喜悦、犹豫、痛苦、焦虑、不舍等情感体验,同时,蕴藉与显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至情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情感相一致的句式变化共同使《洛神赋》成为古今爱情赋之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