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射”和“主皮之射虽有区别,但是究其原始,“礼射”该即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从“习射”的发展过程来看,“主皮之射”以射兽皮为目标,比用擒获来的野兽来习射要简便得多,“礼射”用“侯”来代替兽皮为目标,比“主皮之射”更为进步。《礼记·乐记》说:武王克殷…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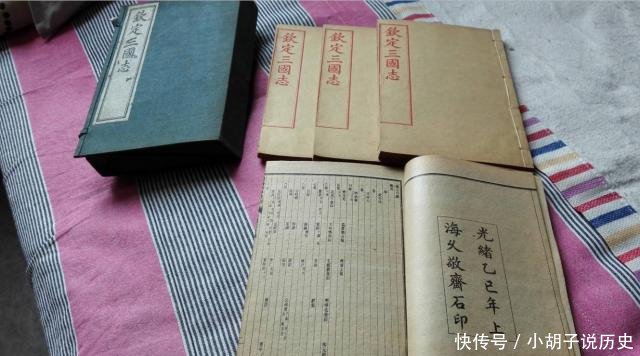
所谓“郊射”,要奏《狸首》和《驺虞》,当即举行“礼射”。“贯革之射”是否即是“主皮之射”,过去经学家还有不同意见,但都是纯粹的习武之射,是无疑的。这里说:周武王克殷后,因推行“礼射”,就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礼射”不一定是武王开始推行的,但是,由于“礼射”的推行,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该是事实。《周礼·乡大夫》郑注:“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郑玄认为“礼射”属于贵族,庶人没有“礼射”,而有“主皮之射”。其实,“礼射”就是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礼不下庶人”,庶民依然行着“主皮之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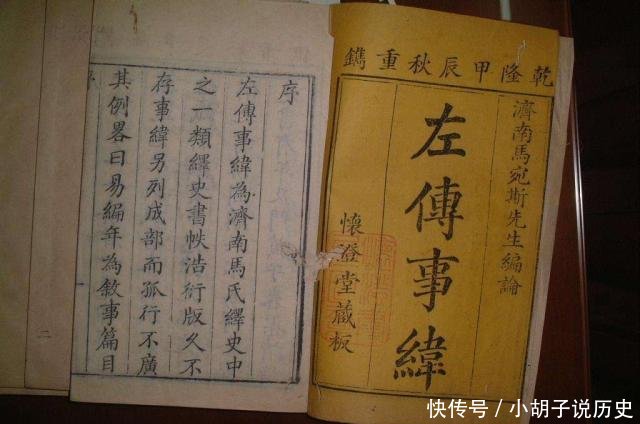
“礼射”的起源于“主皮之射”,从“礼射”用“侯”来代替“主皮之射”所用的兽皮,也可看到。据《周礼·司裘》,天子“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诸侯“大射”用熊侯、豹侯,卿大夫用麋侯,都设有“鹄”。据《考工记·梓人》,大射“张皮侯而棲鹊”,宾射“张五采之侯”,燕射“张兽侯”。据《仪礼·乡射礼》,天子用熊侯,诸侯用麋侯,大夫用布侯画虎豹,士用布侯画鹿豕。据郑玄注解,虎侯、熊侯等,即所谓“皮侯”,是用各种兽皮加以装饰的;画有虎、豹、鹿、豕的“布侯”,即所谓“兽侯”,是在布制的“侯”上画有各种兽的图像的。《仪礼·大射礼》说诸侯“大射”所用的“侯”,有大侯、参侯、干侯。
郑玄认为大侯即熊侯,“参”应读为“糁”,即“杂侯”,“豹鹊而麋饰”;“干”应读为“纤”,即《周礼·射人》“士以三耦射新侯”的“豹侯”,“纤鹊新饰”.各种礼书上所谈礼射用的“侯”,虽然有些出人,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就是比较高级的“侯”直接用兽皮为装饰和制作“鹊”,比较低级的“侯”就只画上某种野兽图像。为什么“礼射*用的“侯”一定要用某种兽皮来装饰或者画上某种兽形呢?因为它原来就是用来代替兽皮的。

《周礼·司裘》郑注说:“谓之鹄者,取名于鸡鹊,鸡鹄小鸟而难中,是以中之为隽.”鸭鹄,《淮南子·汜论训》高注、《广雅·释鸟》认为是鹊,《说文》认为是山鹊,确是一种“小鸟而难中”的。《考工记》说:“张侯而栖鹊”,“栖”原是鸟息止的意思,“鹄”而称“栖”,其原始本为小鸟可知。那么,不仅“侯”的制作,起源于代替兽皮,而且“侯”中设“鹊”,其原始,就是在兽皮中心放着鸡鹊作为标的。射礼“张侯而栖鹊”,就是沿此风习而来。
“礼射”起源于“主皮之射”,其目的也是习射讲武,所以“礼射”除了讲究礼节之外,也还包含有“主皮之射”的内容。《周礼·乡大夫》载: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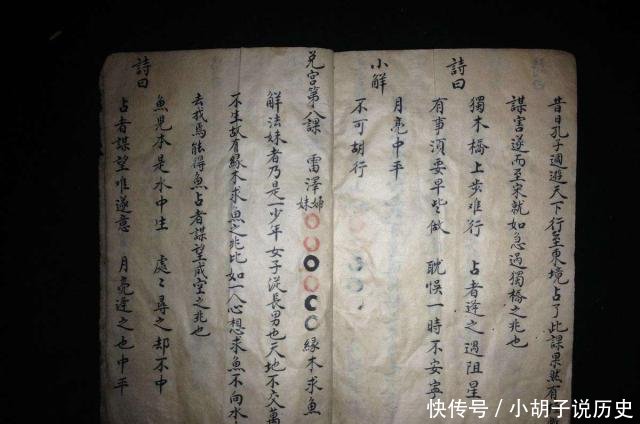
凌廷堪著有《周官乡射五物考》(《礼经释例·射例》附录),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他认为,“一曰和,二曰容”,是指第一番射,这时不统计射中次数,但取其容仪合于礼节,所以称为“和”与“容”;“三曰主皮”,是指第二番射,这时讲究射中贯穿,所以称为“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是指第三番射,这时既要容仪合于礼节,步伐和发射都要合乎音乐的节奏,所以既要有“和容”,又要能“兴舞”。凌氏这个解说,比较通达。但是,既然“礼射不主皮”,为什么射礼的第二番射又叫“主皮”呢?乡射礼射的是布侯而不是皮侯,为什么不叫“主布”而叫“主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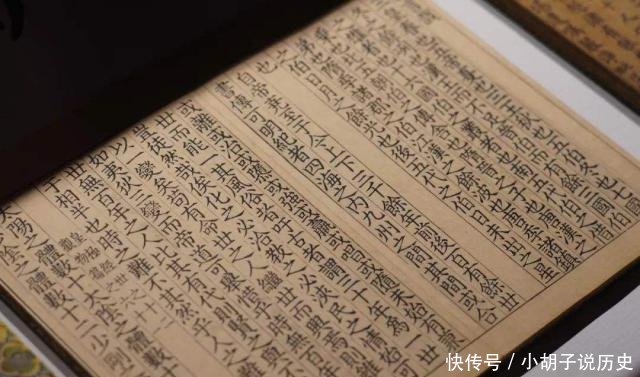
我们认为,礼射的第二番射和“主皮之射”有不同之处,前面已经谈过,“主皮之射”着重在比赛胜负,采取淘汰制的比赛办法,胜者能够再射,败者则被淘汰;而“礼射”着重在训练,采用轮流比射的办法。但是,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有和“主皮之射”相同之处,即主皮之射要射中而贯穿,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是如此,司射在第二番射时发布命令说:“不贯不释”,就是以“贯”作为主要要求的。因为射礼的第二番射有着“主皮之射”要贯穿的特点,亦称为“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