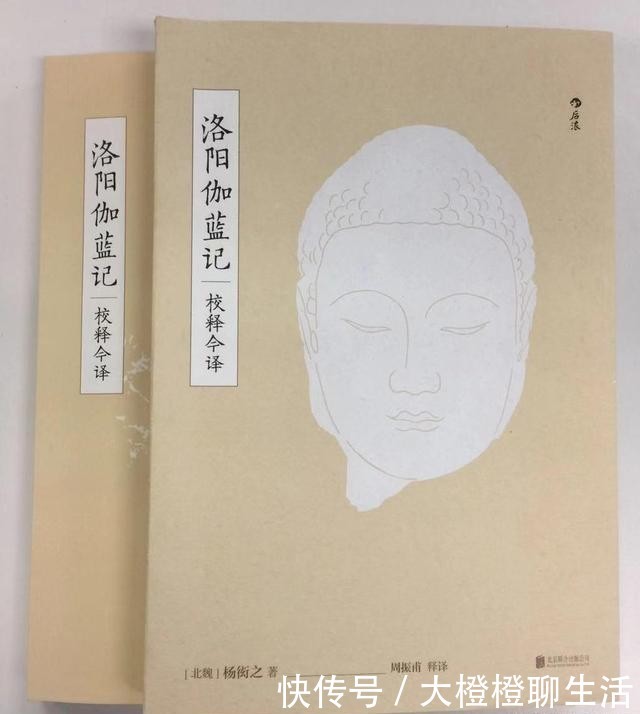
北魏一朝,举国信奉佛教,留下大量佛教文化遗迹。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北魏时代开始开凿。公元495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君主、后妃、官员们,在都城洛阳内及周边兴建了大量寺院,兴盛时达到1367所(据《洛阳伽蓝记》)。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都城,洛阳被废弃,昔日繁华大都市,逐渐沦为废墟。
废墟往往能激发文人的思古幽情。作为魏都的洛阳被抛弃十余年后,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借出差之机重游洛阳,看到这样一片荒凉景象:
他深受启发,遂开始写书,追记洛阳当日城郊佛寺之盛,写出一部流传至今的杰作——《洛阳伽蓝记》。
这部书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此书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中皆有著录,《四库全书》将此时列入史部地理类。但其祖本早已佚失,现所见的《洛阳伽蓝记》都为以宋刻本为祖本,源流颇杂。
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对该书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已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文学、史学、城市规划建筑等方面。
一般认为,在宗教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本书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间。在传播影响上,《洛阳伽蓝记》早有日、韩、英等若干语种译本,在国际汉学界有一定的地位。
后浪出版的这个版本,以周祖谟先生参校各种版本进行的校勘本为底本,周振甫先生对此版本进行了注释全译。名家校释,名家译注,是难得的善本。
但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佛教作宣传,而是通过这些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王公相竞侵渔百姓”(《广弘明集》卷六)的罪恶。例如本书《高阳王寺》及《寿丘里》两节中,他以讽刺的文笔描述了北魏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特权思想和贪鄙性格。如河间王元琛公开对人说:
章武王元融看见元琛的豪富气派以后,更气得“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
胡太后有一次把宫中绢帛赐给百官,任他们自取。别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个豪富陈留侯李崇却贪心不足,“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其他写穷奢极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筑,也颇寓讽刺之意。
本书善于用简短文字叙述述故事和人物。《法云寺》一节,写善吹壮士歌的军乐家田僧超,他追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士声,甲冑之土。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用语不多,颇能显示这个民间音乐家所吹军乐的动人力量。
同篇中写刘白堕的酿酒,烘托尤为神妙:
书中写建筑物也相当精彩。如写永宁寺的九级浮屠,“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使我们惊讶于当时劳动人民建筑艺术的高度水平。从波斯国僧人达摩对此寺及浮屠的赞叹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伟大建筑。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也多次引用本书史料。